•引子•
在我国古代中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素问》篇中, 有这样一段对某种病症的描写: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胭,真脏见,十月之内死。”
即使如此简短的描写,也足以令人想到患者遭受病痛折磨的惨状。古人把这种给呼吸系统造成极大损伤的疾病称为“肺积”,即“阴阳之气郁积于肺”而造成的病变。
现代医学证明,这种在中医上称为“肺积”的疾病, 实际上就是“肺癌”。它是原发于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癌肿,也是最常见的恶性胂瘤之一。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面对这样一种绝症,大夫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慢慢地在痛苦中煎熬,直至死去。
进入20世纪以后,对于肺癌的认识逐渐科学化、理性化, 医学家们想尽种种方法,试图找到攻克肺癌顽疾的途径。失败,尝试,再失败,再尝试,现代医学就这样在坎坎坷坷中一路走到了今天。
研修化学的医学生
埃瓦茨•爱姆布罗斯•格雷厄姆(Evarts Ambrose Graham,1883—1957)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医学家。1883年3月19日,埃瓦茨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他的父亲大卫•格雷厄姆是芝加哥西部地区一位很有名望的外科医生,母亲艾达•巴奈特•格雷厄姆则是一位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公共卫生事业的非凡女性。在这种家庭环境下,埃瓦茨非常自然地走上了外科医生这一人生道路。
1907年,埃瓦茨从拉什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长老会医院,成为了一名实习医生。就在那里,埃瓦茨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人——内科医生罗林•伍德亚特博士。
伍德亚特是一个始终充满激情的人,有着近乎狂热的科学精神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早年师从德国著名医学家弗雷得里希•穆勒教授,穆勒教授在化学方面亦很有研究。伍德亚特受导师的影响,立志要成为一名像穆勒教授那样的“通才”。在伍德亚特的带动下,埃瓦茨也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认识到了化学知识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于是他暂时放下了对临床医学的研究,准备花上两到三年的时间,系统地学习化学。
当时人们对于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联系尚不明了,埃瓦茨这一“超前”的想法让很多人无法理解。埃瓦茨的父亲就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但埃瓦茨最终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研修化学。在此之前,丹麦病理学家克里斯蒂安•芬格已经发表了他在细菌学和传染病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揭示了公共卫生和传染病之间的必然联系。埃瓦茨通过自己的学习,逐渐认同了芬格的观点。当时,包括埃瓦茨的父亲在内的许多外科医生都对外科手术中的无菌消毒技术不甚了然。于是,在父亲为病人动手术前,埃瓦茨不厌其烦地反复要求父亲处理好个人卫生,一度使得父亲大为恼火。在长老会医院的外科手术室里,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在一位年轻人的督促下,极不情愿地反复洗手,有时甚至还要清洗自己的大胡子。
埃瓦茨在化学方面的认真学习,为他打下了深厚的病理学功底。可以说,他以后的所有成功均肇端于此。
1918年,造成全球5 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肆虐一时。当时已经成为美国陆军军医的埃瓦茨奉命前往新泽西州的李堡军事基地参加疫情防治。在此期间,埃瓦茨发现有许多士兵患有脓胸症,而当时大部分医生采用的都是打开病人胸腔排脓的办法,结果许多人在手术结束前就死在了手术台上。埃瓦茨结合自己以前研修的细菌学知识,认为这样做会使得大量病菌侵入肺部,致使病人猝死。于是,他在手术中先把病人的肺门扎紧,阻止了空气进人染病的肺部。这样,士兵就不会在手术过程中猝死了。
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实则是临床医学上的“创举”,不仅验证了病原学说的有关理论,而且给埃瓦茨日后进行首次肺切除手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世界上首次左全肺切除手术
詹姆斯•基尔默是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市的一名产科大夫。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他遭受了慢性咳嗽与发热反复发作的折磨,并且经常感到左胸疼痛难忍。之前他也曾在匹茨堡接受过气胸疗法,但症状一直未见好转。由于基尔默本人毕业于华盛顿医学院,对于这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他就来到华盛顿医学院的巴恩斯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这时是1933年,埃瓦茨当时就在巴恩斯医院任外科主任医师,全程负责了基尔默的诊断与治疗。在对基尔默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后,埃瓦茨断定病人得了支气管鳞状细胞癌。
在征得病人同意后,1933年4月5日,埃瓦茨正式对基尔默进行开胸切除肺叶的手术。
打开病人的胸腔后,埃瓦茨就发现了支气管透镜检查未曾发现的问题。癌变的组织位于基尔默的左肺上叶支气管开口附近,与左主支气管非常接近,而同时叶间裂发育并不完全,如果按照预先的方案,单纯切除左肺上叶,保留下叶,这样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同时,埃瓦茨还发现,在基尔默左肺的下叶也出现了细微的结节性病变。虽然当时埃瓦茨并不能肯定那就是恶性结节,但考虑到病人左肺上叶的情况,下叶恶性结节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冒险保留,一旦癌细胞扩散至右肺,病人就再无治愈的希望了。
在进行快速而又慎重的考虑后,手术台上的埃瓦茨果断地决定对基尔默进行左全肺切除。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例全肺切除的手术。外科界对于这种“大动作”顾虑重重,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大出血、败血症或呼吸衰竭等致命的状况。事后,埃瓦茨回忆说:“之前我只是在动物实验中进行过全肺切除,但是我想:我为什么不能在人身上这样做呢?况且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为了治愈病人,我只能那么做。”
在手术前,埃瓦茨想起了在1918年大流感的防治中自己“独创” 的疗法,认为可以再用一次。于是,他先用一根橡胶管穿过肺门并扎紧,并用血管钳夹住橡胶管的另一端,这样就关闭了整个肺门结构, 防止病菌感染健康的机体组织。当时,在场的其他医生担心这样做会使病人发生肺栓塞,但实际上病人情况很稳定,并没有什么危险的情况发生。
然后,埃瓦茨用电灼刀切除了基尔默的整个左肺,用两道铬肠线对残余组织进行了结扎。同时,埃瓦茨还考虑到了有可能存在的残余癌细胞,就在肺门残端周围插人了7枚氡针。这种局部放射性疗法是埃瓦茨的又一“创举”。
手术进行了1小时45分钟。在此期间,病人的状况一直很稳定。虽然术后由于失血过多,基尔默恢复得很慢,但最重要的是,他还活着。手术成功了!
基尔默在巴恩斯医院一直待到6月18日。他对埃瓦茨未经他授权就切除了他的左肺没有什么抱怨,因为经过对切除部分进行检查后,证实埃瓦茨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基尔默一直活到了1963年,在其78岁的时候因患其他疾病而去世,术后存活了30年之久。
尽管在现在看来,埃瓦茨所进行的第一例左全肺切除手术的成功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但不可否认这一成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第一次向人们证实了全肺切除的可行性,并验证了肺切除手术在治愈肺癌中的价值。在埃瓦茨的鼓舞下,仅在1933年当年,美国便有36例成功的全肺切除手术。
东方的“埃瓦茨”
在埃瓦茨开创性地进行了第一例全肺切除手术后,1941年,在中国北京协和医院里,张纪正医生也进行了中国第一例全肺切除手术。
在今天的天津大理道41号院内,矗立着一幢别致的英国庭院式三层小楼,砖木结构,清水砖墙,坡瓦顶,大屋檐。室内房屋规整,设施完善。周围环境幽静。这就是我国著名医学家张纪正的故居。
张纪正于1905年5月13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县北乡大常疃村。同样是著名胸外科医师,张纪正与埃瓦茨的身世背景却截然不同。埃瓦茨出身名流,有着优越的家庭环境,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张纪正祖上世代务农,从他父亲那一辈起才开始进人旧学堂读书,其母亲则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而这一对普通的中国农村夫妇,在思想上却也有“开放”的一面,他们都很虔诚地信仰着基督教。这也是张纪正和埃瓦茨在身世背景上唯一相同的一点,即自幼都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且都曾经进人过美国长老会学校读书,都有着济世救人的悲悯情怀。
出身贫寒的张纪正在学业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加上他勤奋刻苦,求学之路倒是一路青云,顺利进人齐鲁大学医学院预科。1928年,日本在山东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杀害中国爱国军民3 000多人。这一血淋淋的事件深深震撼了张纪正年轻的心灵。从那时起,他暗暗发誓,要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发奋图强。
这时齐鲁大学因国难停课,张纪正随后转人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读书,并于1931年毕业。他是自己家乡的第一位大学生。
1937年,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张纪正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年,清华大学官费留美项目中有胸外科一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奖学金。张纪正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成为了70多人中唯一被录取的考生,得到了进人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医学院进修的宝贵机会。在密执安州立大学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张纪正又考取了美国专家学会会员的资格。
当时美国有多家医院和研究机构向张纪正发出了邀请函,并承诺提供优厚的年薪和先进的研究设备。张纪正后来回忆说:“如果说我没有心动过,那是说瞎话,但我一闭上眼,就想起了自己饱受苦难的祖国,良心不安。”
就这样,张纪正谢绝了美方的高薪聘请,带着自己的美国妻子(陈必娣),毅然回到了炮火连天的祖国,进人了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于1940年升任外科副教授,并担任胸外科主任。
亚洲第一刀
埃瓦茨在美国进行全肺切除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同为胸外科医师的张纪正感到十分震撼和兴奋。他借助多种渠道详细了解了埃瓦茨的手术过程,对这位美国同行的勇气和高超的技术深表钦佩。所以,当1941年他也遇到了一位和基尔默症状相似的肺癌病人的时候, 张纪正心中不禁涌起了“尝试”的念头。
这位病人叫周庆满,是一位49岁的男性。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他先是感觉到左胸部胀痛,继而低热不断,经中医调理后缓解一段时间,很快又复发。接下来就是不停的咳嗽,直至咳血。他以为自己得了“肺痨”(肺结核),才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
当时在中国,严重的呼吸疾病以肺结核为最多,其次为支气管扩张、肺脓肿等肺化脓性感染疾病,肺癌病例并不多见。北京协和医院也是能做此类手术的为数不多的医院之一,有着当时中国最好的外科医生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张纪正对周庆满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结果发现他得的也是支气管鳞状细胞癌,但病情比基尔默还要严重。癌细胞大面积扩散,肺上叶和下叶分别出现了两个恶性肿瘤结节。针对这样的状况,张纪正意识到病人必须进行左全肺切除,否则无法治愈。
张纪正认真参考了埃瓦茨的方法,也翻阅了许多美国其他成功的手术案例。在经过缜密的论证和充分的准备后,1941年3月14日,张纪正医师对周庆满进行了左全肺切除手术。
肺切除术的关键在于对肺门的精确解剖。张纪正在具体操作时,采取了将支气管与血管分别处理的方法,先将支气管周围的病变淋巴组织摘除,再切除静脉,而后切除动脉,最后将整个左肺用电灼刀切除。张纪正在这次手术中运用的方法后来成为了肺切除手术中的标准操作流程。
这次成功的全肺切除手术挽救了周庆满的生命。术后周先生恢复得很快,而且存活了10年之久,于1951年死于其他疾病。
由于这次手术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例全肺切除手术,所以当时医学界称之为“亚洲第一刀”。张纪正也因此名扬海外。
在做完这次手术后不久,张纪正就来到了天津,与方先之、柯应夔等名医一起创办了天津天和医院并担任院长。当时中国的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下层民众生活日益艰难,食难果腹,更谈不上看病服药。张纪正出身贫苦,自然对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感同身受。他经常免费给那些交不起医药费的贫民看病,有时还赠送给他们药物和盘缠。一时,张大夫的善名传遍了整个天津。
有一次,张纪正坐黄包车出诊时,发现车夫拉车时不停地咳嗽,甚至咳出血来,就赶紧带他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这位车夫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张纪正立即安排他住院,并亲自为他动手术。事后, 痊愈的车夫找到张纪正,感动地不知怎么办才好。
而就是这样一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名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因他美国妻子的缘故,又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受尽了迫害与折磨。
十年浩劫结束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党委给张纪正平了反,恢复了他的工作和职位。劫后“重生”的张纪正好像忘记了当年的那些苦痛的经历,一如既往地兢兢业业;对曾经迫害过、欺辱过他的人,也毫不介意,从来没有做过打击报复的事。对于他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和心爱的医学事业。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可以忘却的。
1984年10月11日,一代名医张纪正与世长辞,享年79岁。
.尾声.
1952年Allison报道了首例右上肺癌做袖式切除,最大程度保留了健肺组织,使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得到改善。2009年,北京胸科医院专家许绍发和刘志东医师带领的胸外科团队为一名68岁的男性患者成功实施了完全电视胸腔镜下袖式肺叶切除术,此举填补了国内在此项技术领域的空白。
2009年,上海胸科医院罗清泉、赵晓菁率领的医师团队运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在胸腔镜下成功地为一名39岁的女性肺癌患者切除了肿瘤。手术中,医生在患者胸部打了4个小洞,每个小洞安装了一个机器人手臂,随后主刀医生在操作台上操控机械手实施手术。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由美国航空航天局等部门联合开发。它的手术特点犹如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的作画手法一样精细。它将传统25cm的大创伤缩小至三四个小孔,对肋骨和肌肉损伤很小,使手术造成的创伤降到最低点。
(审稿专家:陈宝元)
本文版权归海南心路医路医学事业发展基金会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否则将追究违者相关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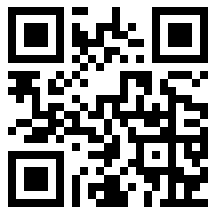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